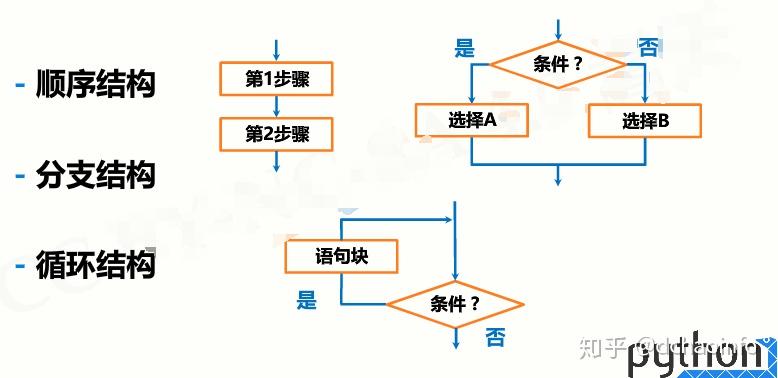随感(三) 关于我们和书
(一)我和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把书作为每天的食物了。这一方面可能得益于我自己在这一阶段抽出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慷慨地投入书海;另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自己前段时间里面对自身主体性方面内容作的一些浅薄的反思。适逢一些别开生面的图书市集举办,身临其境,确实能够感觉到那种沉浸的自如。用“空灵”来描摹这种状态是不恰当的,因为那是一种实然的满足感;用“充实”也不甚合适,因为同样的“充实”能够用在其他各种有意义的活动之上,因之难以突出我“涌现”量级的对书的情感。
于是我宿舍的书桌被装满新书的袋子所包围。我想将它们一一罗列出来,一方面是回溯自己“冲动”的满足,另一方面督促自己去真正与无言的它们发生关系:
-
《在绝望之颠》 ——[法]E.M.齐奥朗
-
《长日将尽》 ——[日]石黑一雄
-
《炒作机器:社交时代的群体盲区》 ——[美]锡南·阿拉尔
-
《世界是如何思考的》 ——[英]朱利安·巴吉尼
-
《无处安放的同情》 ——[德]汉宁·里德
-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 ——[以]施罗默·桑德
-
《日本思想史》 ——[日]末木文美士
-
《社交媒体简史》 ——[英]汤姆·斯丹迪奇
-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
《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 ——[美]斯通、库茨尼克
-
《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 ——[澳]布雷特·鲍登
-
《必然帝国:新世界的奴役、自由与骗局》 ——[美]格雷格·格兰宁
-
《虚无主义》 ——[荷]诺伦·格尔茨
-
《未来道德》 ——[英]大卫·埃德蒙兹
-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美]罗伯特·达恩顿
-
《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 ——[中]赵现海
-
《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 ——[英]玛丽·道格拉斯
-
《奥斯特里茨》 ——[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 ——[中]张珺
-
《古都 虹》 ——[日]川端康成
-
《维塔:社会遗产下的疯癫与文明》 ——[巴西]若昂·比尔
-
《过于喧嚣的孤独》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
《铁路劳工——一位“二战”英国战俘的人生自述》 ——[英]埃里克·洛马克斯
-
《血与砖的文明史》 ——[美]大卫·弗莱
-
《异乡人》 ——[法]加缪
-
《沙特阿拉伯发展史:权力、政治与稳定》 ——[英]蒂姆·尼布洛克
-
《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美]孔飞力
快乐:这些书不仅仅是书,更是我之后一段时间里面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我又能去学习更多的知识,获取更多的视角,体验百般况味的人生。这自然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如果这些书被我束之高阁,那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它们的侮辱:对知识的无效的垄断的想法;与此同时,我从没有卖书或者是借书的想法,我不认为我自己考虑到生活的实际情况应该在知识与热望上吝啬。
庆幸的是,我自己发展出了一套读书的仪式。这套仪式并不类似于所谓的“超验性的”某些信仰或者是神秘话语,我将它视作一种我与书之间的精神桥梁的维系效用。从这段时间开始,我将不再会随意地拆封某一本属于我的新书,除非我已下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对它、对它承载的知识负责;我会看着书的封面与简介、推荐,然后郑重地对书中的知识许诺(这一过程将由形态各异的书的封面来监督)。凡此种种行为结束后,拆封,并且在除致谢、作者心语之后的第一页标注我的名字与日期印章——在时间的另外一端,曲终人散之前,将全书的最后一句话用我能够达到的正楷程度认真书写,并且盖上印章:感谢这本书陪我走过的这段路、教给我的知识;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译者、编辑、美术设计等等。

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需要长期尝试摸索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方法下的读书能够产生什么层次的效果?我非常遗憾地对我之前读过的书、对我接下来将要读的书致歉: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尔尔。在我目前能够接受与建设的层次当中,第一层可说是知识的刚需。这是容易理解的,也是对于大多数学术专著的一个基本要求;第二层可被认为是精神的冲击与想法的涌现。在我的经验当中,这通常能够被体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文学作品的主题与已经通常不是人为框定的,这意味着我能够做出符合我自己想法的解读,同时意味着这样的解读像极了无穷级数:没有尽头;第三层可被认为是其他领域知识的扩展与交叉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天文的:这些是我拓展生命宽度的最重要把手。事实上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第四层是更高学术意义上的研讨与归纳。它鲜明地体现在经典文献与学术专著上,尽管晦涩艰深。于我而言这也是目前我不能企及的高度。但我认为这终究是我必须要跨过的一个坎,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的书。
(二)他们和书
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楚了,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庞老师在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读书的例子:庞老师留法期间“生活拮据”,从来不会施舍外面的乞丐;但是有一位老爷爷希望乞讨一些钱去报刊亭买书阅读时,庞老师没有迟疑地送了出去。
有些事情和想法是不能够用文字的力量去完整地呈现的,但我相当庆幸的是自己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这一群体的集体记忆,能够成为这种最伟大的不可言说的东西的一份子。我粗浅地把它视作“书本的力量”,书本的力量背后蕴含的是精神的感触与灵魂对纯洁与高尚的保持。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为什么能被在大兴区见到的那位清洁工奶奶所深深地震撼:生活可以以任何形式呈现: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所热爱的、我们所困惑的、我们所同情的……但我们永远不能低估、永远不能揣测一个人的灵魂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因为任何一个真正读书的人会在书中真正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那是一种超脱现实的可欲的、高尚的热望。
愿书与我,我与我们永远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