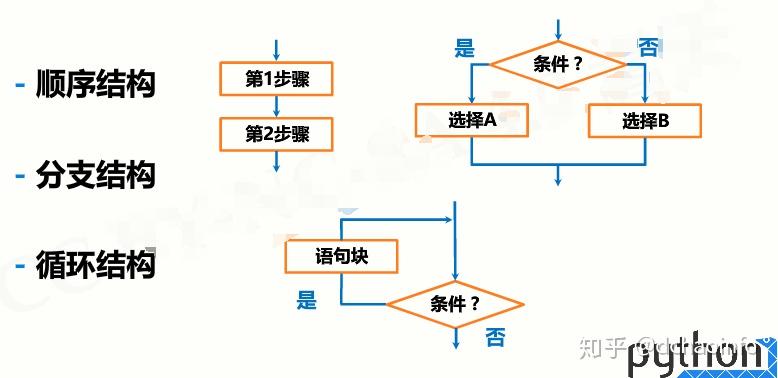战争、记忆与宽恕
主要参考文献/书目:
- 《铁路劳工》
能在兵荒马乱的期末季腾出一些时间来记录自己的感受,我认为还是非常勇敢而真诚的。我真切地认识到,在恰当的时间内记录下自己的想法,不致使它们失真,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件善举。于是我在这里写下《铁路劳工》的一些感受。
(一)与《铁路劳工》的见面
第一次见到《铁路劳工》,我清晰地记得是在西单更新场的图书市集上的C区。那是燕大元照图书编辑部所摆的摊位。在众多端庄的法律专业图书里面,我发现了它,它静静地躺在新书中间,仿佛并没有任何被谁带走的欲望。或许任何的书都没有这样的欲望?我其实不特别在意描述二战的书籍,一方面是自以为自己对二战的了解已经足够了;二方面是以为一直回顾那段历史仿佛对现在没有什么更新的作用了(由于边际效应递减,所能从那些战争的过程当中提炼的故事基本上穷尽了)。但是为了给本家面子,我仍然微笑着带走了它。
在读之前,我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而矛盾的感觉,这种感觉似乎还是不可调解的。一面地,日本军队普遍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残忍、与人性要求相悖;他们的米黄色军服、细长的九九式、锃亮的刺刀、急促而嘶吼般的军令……都无法不能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那种感觉类似于剥离开历史解释的情况之下,猛然见到了红色高棉大屠杀下的遇难者头骨缅怀柜[1]。另一面地,诞生这种历史恐怖的地方,是一片被古旧的神宫、圆锥形雪山与玲珑温良的樱花所包围起来的神圣而朦胧的幻象。长期以来,我无法把这两种意象没有任何违和感地融合在一起,但这本书有意或无意地做了这样的尝试。
(二)一种反思:战争
最残酷的永远是战争:但是我发现,描述战争的残酷,完全不需要动用大规模的战斗场景去描摹战地上的腥风血雨。正如《铁路劳工》所描述的一样。这一方面确与洛马克斯的个人经历有关:部分英国皇家部队并没有组织过什么有效的抵抗;二方面,当洛马克斯站在人生的另一端去回顾曾经的过往,给他内心造成伤痛的罪魁祸首根本不是冰冷的武器,而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内心崩溃。
如果说战争中的主体都能够严格遵循《日内瓦公约》当中的相关准则,那么至少我们能够控制自己对伤痛的感触限制在战地的范畴之上。当我们已经因为战地上纷飞的弹孔、血肉模糊的士兵、破损的建筑等等而肝肠寸断时,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到目前进行的战争中所出现的种种野蛮的行为。显然更高级的“文明社会”具备这样做的“潜质”,几十年前的社会同样如此。今天的我在宿舍的床铺上点亮台灯平静地阅读洛马克斯的回忆录,无论如何也不能穿越回几十年前的欧南路监狱,被踢倒在地,被用鹤嘴锄型的警棍殴打,被看到自己真实的骨头,被打上石膏板,被用纱布捂住面部,被灌注进大量足以致命的水分……我是根本不会体会到这种惨无人道的剧痛的。这甚至不能够用惨无人道来形容,因为这里似乎一遍一遍地突破着作为正常人能够忍受的限度,而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他作为军队的另外一方。
当然,我能够笃定的是,上述的那些超出了一个人的限度的肉体的惩罚还不是整场噩梦的高潮,或许仅仅能够算作一个开始。很小的时候,自己就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我绝对不能够忍受一种能够持续无穷期存在的某种惩罚;无穷期或许仍然是一种不现实的表述;我最厌恶的是被置于某种不确定的境地之中。如果是某个积极的事情或者是某种中性事件的可能结果,比如我应得的奖励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发放;或者是一场面试的结果什么时候才能够公布……它们可能带给我一种一段时间内的思考,这可能是某种不太好的体验,但它无法在我心里长久地形成威胁。然而洛马克斯与我的境遇则截然不同。我会止不住地思考,如果这本书并不是洛马克斯的二战回忆录,而是以他为一个主人公所开展的一系列故事,那么对于那些处在欧南路监狱的战俘们而言,他们的明天是什么样的?我甚至担心见到诸如“突然”“这个时候,一个日本军官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带走了他”等等描述,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死亡威胁[2]。我相信这是最严厉的惩罚,因此当我读到:
休和弗雷德·史密斯都被判入狱十年,比尔·史密斯、斯莱特、奈特、麦凯和洛马克斯都是被判入狱五年。[3]
的时候,我确实和当时的他们一样,“简直都要开心地笑出来了”。
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以国家扩张的名义,为战争赋予某种高于一切的正当性,这事实上是对人类的某种亵渎;与此同时,渲染战争的刺激与快感,并且以之为乐的人,其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助长冷酷的性格,而在于对战争最本质、最源初的残忍、野蛮、持续与掠夺性死亡的异化。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Battlefield V》(《战地5》)。我认为战地5的剧情设定是非常完美的,它的教育意义远远大于它完成任务的紧凑感与成就感,当我看到整个游戏的最后一幕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无法对战争作更多的评价与描述。在《战地5》中如鱼得水的那些竞技玩家们,你们用所谓高超的动作技术夺得耀眼的数据,你们甚至比那些操纵士兵上前线付出生命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主使更为可恶:为了自己的欢娱而一遍一遍地模拟那些自己根本不敢真实面对的景象,并美其名曰“没有阵亡,只有重新部署”,岂不可笑?这或许也是我们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多数希望和平止战,那些根本没有见过战场的人却一味地煽动情绪。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件值得煽动的事情,它展示出了人类社会最野蛮的一面,甚至其他相对低等的动物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我愿用《战地5:猛虎末路》的结尾过场语作结:
1945年春,德意志帝国终于被逼退到曾经的边境内;
民不聊生,生产衰败,全国上下都弥漫着死亡气息。
然而德国尚未投降。
“我们不会屈服,不,绝不!就算我们会被摧毁,也要带上整个世界陪葬,把世界化为火海。”
德国士兵们一直在
无条件服从领导者的誓言之下战斗。
绝大多数人都完全服从命令。
战至最后的命令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牺牲。
我不是世界永久和平的拥趸者;但我同样地厌恶战争。
(三)另一种反思:记忆与原谅
这是我当时选择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当时在阅读书本背后的内容简介与编辑推荐的时候,“后来,在妻子的鼓励之下,洛马克斯决定去见一见这位当时参与折磨他的日本士兵”,这句话带给了我一些震撼。我震撼于洛马克斯同意去见这位日本士兵的勇气,我更震撼于他们之间所达成的那种和解。
我决定从"Rememberence"说起。在这本书的语境当中,"Rememberence"并不是一个轻松活泼的、象征生命力的词汇。这些文字能够唤起我的记忆,是因为我的先辈们与洛马克斯与他的战友们一样,经历过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地狱般的事实,构成了整个民族血淋淋的历史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他们的后人分享着一样的记忆,但是这个层面上的记忆仍然完全不同于洛马克斯的记忆;更普遍地说,是不同于洛马克斯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幸存者的共同记忆。他们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能理解的”国破山河在“的悲戚肃杀之感;也绝对不局限于我们所能理解的部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嗜血成性、惨无人道、人类的历史的罪犯。洛马克斯在战争结束以后,我能够这样认为:他的身体迈入了后二战的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他的精神永远死在了过去[4]。上历史课时,当我们阅读繁冗芜杂的二战历史著作,看着时间轴终于行进到1945年8月的时候,我们会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认为终于能够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仿佛这一页就可以彻底翻过去了一般;但是对于洛马克斯等人来说,他们则永远背着过去的包袱:他们永远活在痛苦的记忆里。我们或许能够从吉光片羽中体认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真实情况,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复刻他们的记忆;他们通常也不会用自己的记忆来扰乱现代人的生活: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通常会湮没在时间长河之中,随着他们一起消逝。那我们应该如何再面对那段记忆呢?是否或许能通过某种疏导的方式,以当事人所应允的方式,得到恰切的归宿?或是将之公布出来以抒心头之情;或是在必要的陪伴中将之赠予冥冥的星河……我没有权利定夺。
一个更值得探讨的话题便是"Forgive"。除去意识形态下所营造的种种人为的对立,我希望考虑的是更一般地基于人的本性的“宽恕”的情感。洛马克斯最终选择宽恕了曾经作为“陪审员”的永濑武志,这篇以温暖收束的故事并非以颂扬洛马克斯的大度人性为旨归;相反,在这个主题上,二人都是主角。文中有一段话能够精确地给出概括:
于是我明白了人生在世,无论做了什么,这辈子都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一个人如果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又没有为此赎罪的话,那么他在下辈子就会被加倍惩罚……即使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理论,但是我知道再惩罚永濑武志,拒绝与他交流,拒绝宽恕他,都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中,我们俩相处得很愉快,他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悔恨,而我们俩也都希望不要让这次见面变得残忍而空洞,而是要赋予它更深远的意义[5]。
对于永濑武志而言,他已被军国主义裹挟犯下可憎的罪行;但面对这既定的历史过程来说,永濑武志没有选择仍然狂热地沉浸在被战争粉饰起来的某种道德正当当中;他也没有选择继续生活在空洞的惭愧当中;相反,他始终背负着自己的罪恶,并且始终为了自身罪恶的宽宥而奔走呼号。这个过程能够同时构成两种情感的基础:(一)从读者的视角来看,他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读者的直截的憎恶与愤恨之情。这能够平滑读者的情绪波动;(二)从洛马克斯的视角来看,他真正需要的是对他之前的惨痛经历的一种真正发自肺腑的认可、理解与同情,甚至是补偿[6]。如果之后永濑武志并未遭受任何显著的痛苦而是平稳地度过余生,那么我们和洛马克斯或许尚不能给他完整的原谅;如果之后永濑武志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完全出于非历史性的原因,那么我们和洛马克斯的同情当中或许会掺杂若干宿命论的嘲讽气息;恰恰相反,他所遭受的身体上与心灵上的折磨正是植根于他曾经创造的罪恶,并且始终致力于罪恶的救赎。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永濑武志的过错是不可弥补的,但是他的为人、他的诚恳与真情是可以信任的。因此,我们或能更好地理解洛马克斯的决定。洛马克斯为永濑武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们的见面缔造了两个时代中属于两个人的最动人、最永久的关于记忆与宽宥的诗篇[7]。
我之前有在认真地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力替我们的父辈原谅曾经的侵略者?我们是否仍然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铁路劳工》所呈现的一种情感状态的组合不在上述的问题域之内。**如果曾经的施暴者能够真正看待历史,能够或多或少地为曾经受其伤害的民族做些什么,我相信今天的事情会有些不同。
非常喜欢全书的结尾,那就以此作结吧:
回想在泰国的时候,当我们参观重开战争墓园时,我和帕蒂两人单独徘徊在墓园里,看着那一排排墓碑,帕蒂产生了片刻的怀疑,她说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不过这种怀疑转瞬即逝,因为我们都知道应该这样做。当时我说:”仇恨,终有一天是要化解的。“[8]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表达我对中文互联网最近所体现出的轻浮、娱乐化以及故作高深的发自内心的厌恶与憎恨。面对来自历史深处的吴哥的眼泪,我们作为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何德何能随意利用波尔布特的相关历史资料去不承担任何责任地满足我们的戏谑与欢娱?可笑。 ↩︎
在这里,类似的情况或许也可以用在晚期癌症病人的身上。我们常常采用“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这样的语句来形容我们所遇到的癌症病人。我在想,癌症病人们除了各种外在的物理化学手段对身体的伤害与折磨以外,面对亲人们对病情消息的封锁,这些病人们是否还仍然经受着心理上的巨大煎熬?这种煎熬并不来自于对亲人的不舍与思念,而是来自于一封没有明确的判决日期但是已经印有官方的印章的死亡判决书。我深深地同情他们。 ↩︎
[英]埃里克·洛马克斯:《铁路劳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178页。 ↩︎
在这里,我所说的”精神永远死在了过去“不能被理解成为一种行尸走肉式的、空洞无神的循环往复的生活而带有贬义的色彩。一个正常的人的心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理解当下所出现的新事物;但是对于洛马克斯来说,将来的一切对他来说将不再有能够触动心灵的改变,他或许会对任何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感。 ↩︎
[英]埃里克·洛马克斯:《铁路劳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6-317页。 ↩︎
这里的认可、理解与同情并不是我们所能够普遍给予的语言支持或者是惯例安慰。节庆日惯例的登门造访等活动并不在此列;公益性质的口述抢救与档案留存能给所有人一种炽热的真诚的感觉。永濑武志的反战呼号就在此列。 ↩︎
特别希望在这里援引在电影《无间道》《无间道3》中出现的佛经原文:——“八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意劫,以此连绵,求出无期”。 ↩︎
[英]埃里克·洛马克斯:《铁路劳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 ↩︎